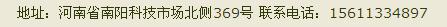赛博格宣言旧文CyberDail
(来源:Cyberpunkcountdown推)唐娜·哈拉韦(DonnaHaraway),“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后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收录于《西米亚人、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再创造》(NewYork;Routledge,),-页。正文:集成电路时代的女性拥有一套共同语言是一个讽刺的梦想。本章试图建立一个忠实于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政治神话。也许比起虔诚的敬拜和认同,亵渎更忠实。亵渎神明似乎是非常严肃对待的事情。无论从世俗-宗教,福音派的美国政治传统,甚至包括社会女性主义的政治热潮,我知道没有比这更好的立场了。亵渎神明可以保护一个人不受内在道德过多的伤害下,同时能满足社群的需要。亵渎神明不是背弃宗教。讽刺是指矛盾不能分解成更大的整体,甚至是辩证的矛盾,是指把不相容的事物连接在一起的张力,因为两者或者所有都是必要的和真实的。讽刺是关于幽默和严肃的戏剧。这也是一种修辞策略和政治方法,我希望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中看到更多的荣誉。在我具有讽刺意味的信仰中,我亵渎的仅是赛博格的形象。赛博格是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一种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体,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体,同时也是虚构的生物体。社会现实是生活的社会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构,是一部改变世界的小说。国际妇女运动构建了”妇女经验”,揭示或发现了这一重要的集体对象。这种经历是一种虚构的,也是最关键的政治事实。解放在于意识的建构,想象的理解,压迫,以及可能性的建构。赛博格是二十世纪后期改变女性经验的小说和生活经历。这是一场关于生与死的斗争,但是科幻小说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界限是一个错觉。(来源:Cyberpunkcountdown推)当代科幻小说充满了赛博格——动物和机器同时存在的生物,他们居住在自然和精心制作的世界里。现代医学也充满了赛博格和有机体及机器之间的联结,每一个都被构想成编码的装置,在一种亲密的关系中,并且拥有一种在性历史上没有产生的力量。赛博格的“性”复苏了一些可爱的巴洛克式的蕨类植物和无脊椎动物(如此漂亮的有机避孕药反对异性恋主义)。半机械复制是解偶联的有机复制。现代生产则似乎是赛博格殖民工作的一个梦想,这个梦想使泰勒主义的噩梦看起来像田园诗般。现代战争是一场机器人狂欢,由C3I指挥控制通信情报编码,这是年美国国防预算中亿美元的项目。我认为赛博格是映射我们的社会和身体现实的虚构物,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资源,可以建立一些富有成效的联结。米歇尔·福柯的生物政治学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赛博格政治的软弱预言。到了20世纪末,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神话时代,我们都是嵌合体,是机器和有机体的理论和虚构的混合体;简而言之,我们是半机械人。这个机器人是我们的本体论;它给了我们政治。赛博格是想象和物质现实的浓缩形象,两者结合在一起构建任何历史转型的可能性。在”西方”科学和政治传统中——种族主义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进步传统;将自然作为文化生产资源的占有传统;从他人的反映再现自我的传统——有机体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触即发的边界战争,而它的利害关系一直是生产、繁殖和想象的土壤。这一章是一个在混乱的界限中寻求快乐的论证,以及在它们的建构中寻求责任的论证。这也是一种努力,以后现代主义、非自然主义模式和乌托邦传统的方式,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和理论作出贡献,这种乌托邦传统是想象一个没有性别的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是一个没有起源的世界,但也可能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世界。机器人的化身是救赎历史之外的。它也没有在恋母情结的日历上标记时间,试图治愈口头共生乌托邦或后恋母情结启示录中可怕的性别分裂。正如佐伊?索福利斯(ZoeSofoulis)在她未发表的手稿《雅克?拉康(JacquesLacan)、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Klein)和核文化——Lacklein》(nuclearculture)中指出的那样,半机械人世界中最可怕、或许也是最有希望的怪物,体现在非恋母情结的叙述中,带有一种不同的压抑逻辑,这是我们为了生存而需要理解的。(来源:Cyberpunkcountdown推)半机械人是后性别世界中的一种生物,它与双性恋、前恋母共生关系、未异化的劳动或其他通过将各部分的所有力量最终挪用到一个更高的统一体而获得有机整体的诱惑毫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赛博格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起源故事——这是一个“最终”的讽刺,因为赛博格也是“西方”逐步升级的抽象个体化统治的可怕的末日终结者,一个终极的自我解放,一个活在太空中的人。一个起源故事在西方,人文主义的意义取决于原始的统一,充实,幸福和恐怖的神话,代表所有人类必须从阴茎的母亲分离,个人发展和历史的任务,两个强有力的神话铭刻我们在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希拉里·克莱因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精神分析学,在他们的劳动、个体化和性别形成的概念中,都取决于原始统一的情节,而差异必须由此产生,并参与到逐步升级的女性/自然统治的戏剧中。赛博格跳过了西方意义上的原始统一、与自然认同的步骤。这个不合法的承诺可能会颠覆它的星球大战目的论。赛博格坚决地致力于偏袒、讽刺、亲密和反常这些人性集合体。它是对立的、乌托邦式的、完全没有纯真的。赛博格不再是公共和私人两极分化的结构,它定义了一种技术民意调查,其部分基础是奥伊科斯家族(oikos,thehousehold)社会关系的革命。自然和文化被重新改造,一方不再是另一方占有或合并的资源。在赛博格的世界里,由部分组成整体的关系,包括极性和等级统治的关系,是有争议的。不同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的希望,机器人不指望它的父亲通过修复花园来拯救它;也就是说,通过制造一个异性恋伴侣,通过完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个城市和宇宙。艾伯格并没有梦想有机家庭模式的社区,这次没有恋母情结的项目。机器人不会认出伊甸园(年电影);它不是由泥土构成的,也不会梦想着回到尘土中。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看看赛博格能否颠覆世界末日----在命名敌人的狂躁冲动中重返核尘世。半机械人不是虔诚的,他们不会重新记忆宇宙。他们警惕整体主义,但需要联结——他们似乎对统一战线政治有一种自然的感觉,但没有先锋党。当然,半机械人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是军国主义和父权资本主义的私生子,更不用说国家社会主义了。但是私生子往往对自己的出身极不忠诚,毕竟,他们的父亲是无足轻重的。(来源:Cyberpunkcountdown推)在本章的最后,我将回到半机械人的科幻小说,但是现在我想说明三个关键的边界分析,这些分析使得下面的政治-虚构(政治-科学)分析成为可能。到了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的科学文化彻底突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最后的独特滩头已经被污染,如果没有变成游乐园-语言工具的使用,社会行为,心理事件,没有什么真正令人信服地解决人类和动物的分离。许多人不再觉得需要这样的分离;事实上,女权主义文化的许多分支肯定了人类与其他生物联系的乐趣。争取动物权利的运动并不是对人类独特性的非理性否认;它们是对破坏自然和文化的行为之间的联系的明确承认。过去两个世纪的生物学和进化论同时产生了现代有机体作为知识的对象,并将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界限缩小到一个微弱的痕迹,这种痕迹重新铭刻在生命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或专业争论。在这个框架内,教授现代基督教创世论应该作为一种形式的虐待儿童的斗争。生物决定论思想只是科学文化中为论证人类动物性意义而开辟的一个立场。激进的政治人物有很大的空间去争辩被突破的界限的意义。赛博格恰恰出现在神话中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突破的地方。赛博格的信号不是将人与其他生物隔离开来,而是分散的、令人愉快的紧密耦合。兽交在这个婚姻交换的循环中有一个新的地位。第二个有漏洞的区别是在动物-人类(有机体)和机器之间。控制论之前的机器可能会产生闹鬼的人类行为,这意味着机器里是有鬼魂的幽灵。这种二元论构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由一个辩证的后代根据品味而解决的,其也被称为精神或历史。但基本上机器不是自动的,自我设计的,自主的。他们无法实现人类的梦想,只能嘲笑它。他们不是人,不是他自己的作家,而只是那个男权主义繁殖梦想的讽刺漫画。认为他们在其他方面是偏执狂。现在我们不那么确定了。二十世纪后期的机器已经完全模糊了自然与艺术、思想与身体、自我发展与外部设计之间的区别,以及许多其他用于生物体和机器的区别。我们的机器是令人不安的活跃,而我们自己是令人恐惧的惰性。………………………………………..概括地说,某些二元论在西方传统中一直存在;它们都是系统地存在于支配妇女、有色人种、自然界、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中——简言之,支配所有与其他人一样构成的、其任务是反映自我的人。在这些令人不安的二元论中,最主要的是自我/他者、心灵/身体、文化/自然、男性/女性、文明/原始、现实/外表、整体/部分、动因/资源、创造者/制造者、主动/被动、对/错、真理/幻想、托塔夫部分、上帝/人。自我是不被支配的那个,是被另一个虚拟的未来掌握着。他知道被支配的感受,这就给了自我的自主性一个谎言。合一意味着自主,强大,成为上帝;但合一意味着幻想,因此要与其他人一起参与末日的辩证。然而,“他者”是多重的,没有明确的界限、磨损、虚无。一个太少,两个太多。(译者:人最终无法理解彼此,但至少我们在某个时刻相互交叉过)(来源:GameInformer官推)高科技文化以有趣的方式挑战这些二元论。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中,谁是创造者,谁是被创造者呢,我们还未分清楚。就目前,还不清楚思想意识是什么,身体在机器中获得编码—解决—实践的的路径是什么。实际上,就我们在正式论述(例如,生物学)和日常实践(例如,集成电路中的家庭作业经济)中对自己的了解而言,我们发现自己是半机械人、混血儿、马赛克、嵌合体。生物有机体已经变成了生物系统,就像一种生物通讯设,相互连接。在我们关于机器和有机体、技术和有机体的形式知识中,没有出现基本的、本体论的分离。但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银翼杀手》中的复制人瑞秋,却代表了一个半机器人文化的恐惧、爱和困惑。当然,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与工具的联系感增强了,以致许多电脑用户经历的恍惚状态已经成为科幻电影和文化笑话的资料。也许截瘫患者和其他严重残疾的人可以(有时确实如此)拥有与其他通讯设备进行复杂杂交的最强烈体验。安妮·麦卡弗里(AnneMcCaffrey)的前女权主义作品《唱歌的船》(TheShipWhoSang,)探索了一个半机械人的意识,一个严重残疾儿童出生后形成的女孩大脑和复杂机械的混合体。性别,性,身体化,技能:所有这些在故事中都被重构了。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应该停留在皮肤上,或者至多包括其他被皮肤包裹的生物?从17世纪的动态链接库开始,机器可以被赋予活灵活现的灵魂,让它们说话或移动,或者解释它们有序的运动和心智能力。或者生物体可以被机械化-还原为身体,被理解为思想的源泉。这些机器/有机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过时,没有必要。对我们来说,在想象和其他实践中,机器可以是假肢装置,亲密好友,亲近自我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有机整体论来赋予不可渗透的整体性,整体女性和她的女性主义变体(突变体?).让我通过对我的第二组文本----《女性主义科幻小说电子怪物逻辑的非常片面的解读来总结这一点。生活在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的半机器人使得男人或女人、人类、人工制品、种族成员、个体或身体的状态变得非常成问题。凯蒂·金阐明了阅读这些小说的乐趣并不是基于身份认同。学生们第一次看到乔安娜·拉斯,那些学会了毫不畏缩地接受詹姆斯·乔伊斯或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的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理解《阿丽克斯历险记》或《女人》。女性男人》讲述的是一个基因型的四个版本的故事,所有这些基因型都相遇,但即使放在一起也不能组成一个整体,解决暴力道德行为的困境,或者消除日益增长的性别丑闻。女性主义科幻小说塞谬尔·迪兰尼》,特别是《Neveyon故事集》,通过重演新石器革命,重演西方文明的奠基动作,以此来嘲笑起源故事,颠覆它们的合理性。小詹姆斯是一位作家,她的小说被认为是特别有男子气概的,她的真实性别被揭露了,她讲述了基于非哺乳动物技术的生殖故事,比如男性育儿袋和男性养育的世代交替。约翰·瓦利在他的女权主义探索盖亚中构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半机械人,一个疯狂的女神-行星骗子-老妇人-技术装置,其表面上产生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后半机械人共生体。奥克塔维亚·巴特勒(OctaviaButler)写道,一位非洲女巫用她的转化力量对抗她的对手(《野生种子》(WildSeed))的基因操控,用黑色魔法将一位现代美国黑人女性变成奴隶,她与白人主人——祖先的关系决定了她自己出生(《家族》)的可能性,以及对一个被收养的跨物种儿童的田园生活和社区的模糊洞察力,这个跨物种儿童后来认识到enem是自我(《幸存者》)。《黎明》()是《异种繁殖》系列的第一部,巴特勒讲述了莉莉丝·伊亚波的故事。伊亚波的个人名字让人想起了亚当被遗弃的第一任妻子,她的姓氏标志着她是尼日利亚移民之子的遗孀。莉莉丝是一位黑人女性,她的孩子死了,她通过与外星爱好者/救援者/毁灭者/基因工程师的基因交换来调解人类的转变,这些人在核浩劫之后改造了地球的栖息地,并强迫幸存的人类与他们进行亲密的融合。这部小说追问二十世纪末种族和性别构成的神话领域中的生殖、语言和核心政治。(来源:Cyberpunkcountdown推)因为它特别丰富的越界,冯达麦金泰尔的超光速可以结束这个有希望的和危险的怪物的删减目录,帮助重新定义体现和女权主义写作的乐趣和政治。在一部没有人物是简单的人类的小说中,人类的地位是非常有问题的。虎鲸是一个基因改造过的潜水员,可以与虎鲸对话并在深海环境中生存,但她渴望作为一名飞行员探索太空,因此必须植入仿生装置,危及她与潜水员和鲸目动物的亲密关系。病毒载体携带新的发育代码,移植手术,植入微电子设备,模拟双精度设计,以及其他手段都会影响转变。通过接受心脏移植和一系列其他变化,使得患者能够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在运输中生存下来,拉斯尼亚成为了一名飞行员。拉杜·德拉库在他的外星球上躲过了一场由病毒引起的瘟疫,他发现自己拥有了一种改变了整个物种空间感知边界的时间感。所有的角色都在探索语言的局限性,交流经验的梦想,以及限制、偏爱和创作的必要性,即使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变化和联系的世界。在另一个意义上,超光速也代表着机器人世界的明确矛盾;它在文本上体现了女权主义理论和殖民话语在我在本章中提到的科幻小说中的交叉点。这与许多“第一世界”的女权主义者试图压制的漫长历史有关,包括我自己在阅读《超光速》(Superluminal)时被佐伊·索福利斯(ZoeSofoulis)要求解释之前的经历。索福利斯在世界体系中占有不同的地位,这让她敏锐地意识到所有科幻文化的帝国主义时刻,包括女性科幻文化。出于对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敏感,索夫利斯更容易记起麦金太尔在电视剧《星际迷航》中扮演的角色,即编剧科克船长和斯波克,而不是她在《超光速》中重写罗曼史。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怪物总是定义着社区的界限。古希腊的半人马和亚马逊人通过破坏婚姻和带有兽性和女性的武士的边界污染,确立了希腊男性人类中心民意的限度。在近代早期的法国,未分离的双胞胎和雌雄同体是混乱的人类材料,他们以自然和超自然、医学和法律、预兆和疾病为基础,所有这些对于建立现代身份都至关重要。猴子和猿类的进化和行为科学标志着二十世纪后期工业身份的多重边界。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怪物定义了完全不同于世俗小说《男人和女人》所提出的政治可能性和限制。把半机械人的形象当作我们的敌人以外的其他东西来对待,会产生一些不可估量的后果。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都潜意识认为身体是权力和身份的地图象征。半机械人也不例外。机器人的身体不是无辜的;它不是诞生于花园;它不寻求单一的身份,因此这种欣慰产生无休止二元论对抗(或直到世界末日),而讽刺是理所当然的了。一个太少,两个只是一种可能。对技能和机器技能的强烈喜爱不再是一种罪恶,而是一种化身。机器不是一个可以被激活、崇拜和支配的机器。机器就是我们,我们的过程,我们身体化的一个体现。我们可以对机器负责,它们不会支配或威胁我们(译者注:赛博格乐观主义)。我们对界限负责,我们就是界限。直到现在(很久很久以前),女性化身似乎是被赋予的,有机的,必要的;而女性化身似乎意味着母性技能及其隐喻意义。只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们才能在机器中获得强烈的快感,然后借口说这毕竟是有机活动,适合于女性。半机械人可能会更认真地考虑片面的、流动的、有时是性和性体现的方面。性别毕竟可能不是全球认同,即使它具有深远的历史广度和深度。什么算作日常活动,什么算作经验,这个在意识形态上充满争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用机器人形象来解决。女权主义者最近声称,女性被赋予了日常性,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比男性更能维持日常生活,因此潜在地拥有一种特权的认识论地位。这种说法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那就是将无价值的女性活动公之于众,并将其命名为生命的基础。但是生命的土地呢?那些对女性的无知,对知识和技能的排斥和失败呢?那么,人们如何获得日常能力,如何知道如何建造东西,如何拆解东西,如何玩耍呢?那么其他实体又如何呢?赛博格性别是一个局部的可能性采取全球复仇。种族、性别和资本需要一个关于整体和部分的半机械理论。赛博格没有动力去产生完整的理论,但是他们有一种亲密的体验,关于边界,他们的建构和解构。有一个神话系统正等待着成为一种政治语言,以便建立一种看待科学和技术的方式,并挑战统治的信息学——以便有效地发挥作用。最后一个形象有机体和有组织的整体政治依赖于再生的隐喻,并且总是需要生殖性的资源。我认为赛博格与再生有更多的联系,但是他们对生殖基质和大多数生育持怀疑态度。对于蝾螈来说,损伤后的再生,如肢体的缺失,包括结构的再生和功能的恢复,以及在原损伤部位不断产生孪生或其他奇怪的地形。再生的肢体可以是巨大的,复制的,有力的。我们都深受其害。我们需要重建,而不是重生,我们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对一个没有性别的怪异世界的希望的乌托邦梦想。赛博格意象可以帮助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两个关键的论点:第一,产生普遍的,总体化的理论是一个主要的错误,它忽略了大部分的可能性现实,是当下总是出现的;第二,承担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的责任意味着拒绝反科学的形而上学,技术的魔鬼,因此意味着拥抱巧妙的任务,重建日常生活的边界,与其他人的产生一些联系,与我们所拥有的部分需要发生关系。科学和技术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可能性手段,也是一种复杂支配的矩阵工具。赛博格意象可以为我们指出一条走出二元论迷宫的道路,在这个迷宫中,我们已经向自己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工具。这不是一个共同语言的梦想,而是一个强大的异教徒杂语的梦想。这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用方言说话的想象,让新右派的超级储蓄者感到恐惧。它意味着建造和摧毁机器,身份,分类,关系,太空故事。尽管两者都受到螺旋舞蹈般的束缚,我宁愿做一个半机械人也不愿做一个女神。(翻译有误,请指正,见谅)周末愉快*本文由CyberDaily作者See编译,转载请联系后台。See
上一篇文章: 从凶猛到美丽,这些照片为你描述了真正的自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CyberDaily作者,
转载请注明:http://www.bktzq.com/ways/13092.html